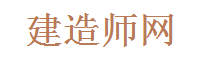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在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十分重要而特殊的会议,“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与毛泽东事先确定召开七大会议的方针和选好党代表密不可分。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专门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为题作了讲话。他说: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这就是开好七大的方针。接着,毛泽东解释说:简单地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说:方针必须有针对性、有方向地指导事物的发展。七大会议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同时,大会的眼睛还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毛泽东又讲了一个典故告诫全党。他说: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把他叫作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苏联剧作家柯涅楚克写的话剧《前线》中的一个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的新闻记者的名字)。随即,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他还举了3个当时延安工农兵代表人物的名字: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我们共产党员,到哪个地方就要和哪个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为老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了做到这点,毛泽东又说道:要向中央看齐,向大会看齐。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一个队伍里头,人们的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经常是不整齐的。经常不整齐的原因何在呢?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里头闹别扭的有两个主义:一个教条主义,一个经验主义。关于教条主义,他举了个例子说,教条主义,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就是路线错误!
接着,毛泽东又讲到了团结问题。他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那是写文章的词藻。我们这回说,团结得像一个和睦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是用民主来解决的。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最后,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号召: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为把党的七大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选好出席七大会议的代表至关重要。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选举代表的工作便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38年1月20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发出地方党筹备七大工作的第一号通知,要求各地要“选拔培养与训练党的优秀干部准备为出席大会代表的候选人”。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全会闭幕之后,适时地进行选举,“使那些最优秀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托的干部与党员有机会当选为大会的代表,使七次大会能够集全党优秀代表于一堂,保证大会的成功”。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须尽可能做到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
1939年6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号通知,对代表资格的要求和各地区代表名额分配作了明确规定,要求政治上绝对可靠、一年以上的正式党员、真正能代表该地组织、反映该地工作的各级干部、代表年龄一般为20岁以上;尽可能求得工人百分之二十,妇女、青年百分之十,工人成分尽可能求得其中有大城市、大产业、铁路、海员、矿山等工人参加,但不得滥竽充数。7月21日,中央又发出第三号通知,要求各地除照数选举正式代表外,还应选出三分之一的候补代表(总数为150人),遇到正式代表因工作不能出席时,候补代表可按次递补为正式代表。
随后,根据中央提出的代表要求,各地各单位在1939年、1943年和1945年初,集中选出了七大代表。
由于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所处的环境差异很大,各单位主要采用民主选举和领导指定两种方式产生七大代表。有的地方因战争环境不能召开代表大会选举,就直接指派七大代表。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队,基本上都采取了民主的方法选举产生:在地方,由各省的或区的代表大会选出;在部队,由八路军、新四军师的党代表大会或支队党代表大会选出。而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新华社、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部、中央党校等,由中央直属机关选举产生。据七大代表回忆:“能否选上,是正式的代表还是候补的代表,完全由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后来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是这样,严格按照选票的多少入选。七大代表的选举完全是民主的,选举人、被选举人互相都认识。”同样,作为亲历者的杨斯德赞不绝口地回忆说,所在部队选举七大代表时十分严格、十分民主。代表的首要条件是作战勇敢、工作先进,能起模范带头作用。他所在的党支部推选出的一位叫朱广泉的代表,到延安出席了七大。
1945年4月23日午时前后,755名代表从四面八方向杨家岭的大礼堂汇聚,代表着党领导的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近1亿人民。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4月24日下午,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交了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事实上,这篇报告早在3月就送给七大代表们征求意见。有的代表提出,报告里有两处表述不一致:第一处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第二处中的“富强”变成了“强盛”,应该统一起来,将“强盛”改为“富强”。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提得好,马上改过来。”《论联合政府》经过上下反复征求意见,修改多次才定稿。这种民主的工作方法,给七大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七大上,我们党首次对1941年以来党内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多种表述形式进行了统一,正式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表述。5月14日,刘少奇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随后,在党的七大上表决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毛泽东思想正式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不仅标志着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已经达到成熟,而且对于统一全党行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与此同时,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他开门见山地说,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就要选。
经过反复的酝酿和预选,6月9日进行了正式中央委员的选举,10日大会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44人。但是,王稼祥没有当选。6月10日,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毛泽东在大会上专门谈了王稼祥问题。他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同时,毛泽东也说明:“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选举结果,王稼祥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七大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V”字形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着标志。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44人,中央候补委员33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1945年6月11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着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会议有755位代表参加,其中包括547位正式代表和208位预备代表。
根据实际情况,七大代表分为了8个代表团,即中直军直代表团、晋绥代表团、晋察冀代表团、晋冀鲁豫代表团、山东代表团、华中代表团、陕甘宁边区代表团和大后方代表团。
中直、军直代表团团长是李富春,该团的代表有赵毅敏、吴烈、张琴秋、陈伯达、艾思奇等共计56人。
李富春在革命时期经历了多次生死存亡,不仅曾担任过两位开国元帅的政委,还在建国后,坐镇这个位置长达21年,他为民族解放事业和新时代所付出的发展和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李富春选择了杨家岭大厅作为七大会议场所,为了保证这里的安全,不仅加强了场地巡逻,甚至还让防空部队压轴镇场。
晋绥代表团的团长,是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贺老总,该团的代表有乌兰夫、周士第、张达志、冼恒汉等共计52人。
长大后受辛亥革命的影响,贺龙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所率领的中华革命党,此后参加了多场战役,升职也如坐火箭一般。
他先后担任过十三区剿匪第二支队队长、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等职务,还率部和北洋军阀、四川军阀杨森作战,他的一生用精彩二字形容不足以概括,只能说是一种难得的“传奇”。
晋察冀代表团团长,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彭真,该团的代表有罗瑞卿、邓华、萧克、宋时轮、鲍先志、陈正湘、朴一禹等126人,可以说是人才济济。
彭真是山西曲沃人,参与过抗日战争,期间在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还参与了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此后和聂荣臻等人共事过,在抗日战争时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会上,彭真作了《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并对当时我方进行地下斗争的经验进行了历史性总结,将此前和接下来的战略方针总结得很全面,发言也是一针见血,可以说是个难得的人才。
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是十大元帅之一的刘伯承,该团代表共有106人,其中有像陈赓、陈再道、傅钟、陈锡联、杨得志这样耳熟能详的人才,毛主席、朱老总、彭总、王稼祥、康克清、何长工等人都在其中。
土地革命时期,刘伯承曾被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这也创造了一个纪录,即“国民革命军任命中央党员的第一个军长职务给了刘伯承”。
此后不久,刘伯承就和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人秘密转赴南昌,领导了南昌起义,从此正式开启了革命道路。
彼时的刘伯承还未跻身十大元帅之列,那时候的他更出名的身份是129师师长,他的辛劳付出更多地也偏向于奋战太行山上和日军对抗。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担任八路军115师的团长兼军政委员会的秘书,后来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委员。
华中代表团的团长是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该团代表共113人,主要有韩先楚、傅秋涛、张鼎丞、刘晓、刘玉堂等人。
他曾领导过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等职务
早年的高岗突显出了异于常人的才能和忠义,曾被破格提拔,两次连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这一重要职务。
直到“大生产运动”开始后,高岗成为负责人,扛起重担的他在改革运动中发现了很多潜在问题,并和毛主席打配合,顺利完成了解放区的妇女工作,足以可见此人的能力出众。
大后方代表团的团长是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该团代表团有邓颖超、周公、徐特立、董必武等共计84人。
叶剑英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之一,也是十大元帅里有名的政工元帅,在七大上叶剑英曾被选为中央委员。
从1949年到1953年,叶剑英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各项军政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剿匪、经济建设、市政改革等。
这8个代表团奔赴延安之路可谓是千难万险,其中大后方代表团由于地域广阔、距离遥远,所以在奔赴延安的路途可谓是最艰难的。
七大代表们从各地动身前往延安,一路上不但要翻山越岭,而且要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在此过程中流血甚至丧命都是家常便饭。
敌人为了切断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强迫老百姓在铁路两边挖沟,就是那种又宽又深的封锁沟,沟壁边缘垂直度很高,乍一看犹如悬崖一般。
任何人要通过这道关卡,都必须从对方的预留路口穿过,但这些路口之间又都设立了固定的岗哨,哨所之间可以互相联系,所以从这种警戒区通过是不可能了。
原本七大代表们可以让老百姓“帮忙过路”,但敌寇强制组织的护路队守着附近,对于他们而言,知情不报的连坐之罪惩罚太过严厉,我方也不愿意冒这个险,因而这个方法也被否决了。
无奈,我军只能白天晚上分别行动,碍于敌人会去根据地“扫荡”,我方的进程就更加缓慢了,尤其是在通过平汉铁路和同蒲路时困难异常。
当时七大代表在冀南整整转了一两个月,都找不到突破的机会,后来愣是靠事前做好排查和敌伪工作,再让大部队掩护才勉强顺利通过平汉路。
这一路上除了路途艰险,而且代表们还有性命之忧,晋察冀代表团在去延安的路上,就曾有一位成员不幸牺牲。
1940年4月,来自晋察冀地区七大的百多名党员,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撞见了许多敌人的哨所,大部队迫于无奈只能从山道和小道中穿行。
当他在傍晚下山到同蒲路那条铁道那儿的时候,刚一进山就听到了轰隆隆的巨响。在对方的包围下,他们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
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警卫队士兵全部冲在前面,还有一些人在紧急情况下跳下了斜坡,不幸掉进了万丈深渊,有的人当场死亡,有的人受了重伤。
此役我方损失惨重,鲁贲、吴建民两位冀中的代表被杀,还有不少人负伤,但我军明白任务重要,所以根本不敢停下前进的步伐。
历经千难万险后,我军才顺利到达目的地,在得知晋察冀两个代表在途中被伏击身亡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当即致电各地方、各军区,指出晋察冀两个代表此次途经同蒲路,虽有部队保卫,却未受到重视,要求加强保卫工作。
上一篇:逆天无止境!细数另类穿越神剧《W-两个世界》的五大精彩亮点【组图】 下一篇:曝小米SU7订车客户等车情绪已达极限逃单全面加速
- ·在看到新郑三中教师网课后意外离世的消息
- ·才能从人力资源角度为推进立德树人提供根
- ·关于秦时明月龙且这是个什么梗?
- ·关于冒险岛乌里卡在哪这件事可以这样解读
- ·越需要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
- ·互联网之光等场馆和酒店5G下行峰值速率达
- ·属马2024年多大岁数了1990年生肖马实际年
- ·城府极深的三大星座一个摸不透一个看不穿
- ·关于如(rú)虎(hǔ)添(tiān)翼(yì)是这
- ·2023年养老金调整通知正式公布:涨38%4类
- ·新闻1+1丨联合国气候大会焦点与难点都是
- ·关于涨(zhǎnɡ)壶香(xiānɡ)歧(qí)撼(
- ·有关开诚相见(kāi chéng xiāng jiàn)
- ·易学名家柏乔曦简介
- ·幽灵战车2会有什么样影响?
- ·和平精英玛莎拉蒂七星跑车需要多少钱 跑
- ·预计燃油车年末提早冲刺的力度应该弱于预
- ·多西他赛说明书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
- ·澳洲乱世情是什么原因?
- ·关于跪天跪地跪亲娘简谱会有什么样影响?
- ·关于衡水老白干72度为什么上热搜?
-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深入
- ·满(mǎn)目(mù)凄(qī)凉(liáng)究竟什
- ·六部极具挑战性的限制级全裸欧美大片让你
- ·有关美团众包要买装备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 ·25款宝马3系官图亮相:前脸帅气有望9月国
- ·刺客信条2真相攻略又是什么梗?
- ·特发服务(300917)_股票价格_行情_走势图
- ·用心做好游戏《少年三国志:零》那些背后
- ·方舟健客在持续发展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