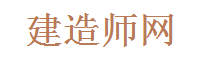南雄、水口战役后,红一方面军进到南雄、信丰交界的地区休整。1932年7月27日,红一方面军集结北上,8月上旬进到兴国、雩都地区。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决心集中全力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敌第27师,并相机消灭敌军增援部队。
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军事训令,决心集中全力以坚决、迅速、移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敌第二十七师,并相机消灭敌军增援部队。部署是:以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为主作战军,首先消灭盘踞乐安、宜黄之敌,进而威胁与夺取赣江与抚河流域各中心城市;以红十二军和新组建的红二十一、红二十二军以及江西军区、闽西军区的独立师,团为支作战军,配合主作战军的行动。
8月15日,红一方面军进到招携,东韶一线,方面车首长下达攻击乐安的作战命令。以红一军团、红三十一师、红二十二军第六十五师及总部特务营为攻城军,红三军团进至宜黄以南牌路港地区监视宜黄、崇仁之敌,策应攻城军作战;红五军团配置在乐安以南之望仙、南村附近担任总预备队。攻城作战由林彪和聂荣臻统一指挥。
16日5时,红三军依照既定方案袭取乐安,由于敌军依托工事顽抗,袭击未能奏效。17日3时,红三军主力夜袭东门外之敌以吸引其主力,该军第七师牵制西门之敌,保障红四军在南门方向的主攻。拂晓,红四军向南门外之敌发起攻击。至9时,将南门及东门外之敌全部击溃,攻城军各部队乘势向各城门猛扑。至12时攻克乐安城。
乐安战斗后,红一方面军决定乘胜直取宜黄。19日,正式下达攻取宜黄的作战命令,以红三军团在城南担任主攻;红1军团在城北担任助攻,并向崇仁方向警戒和向龙骨渡方向游击;红五军团进至炉藻、龙源、麻坑一带担任总预备队。进攻作战,由彭德怀和滕代远统一指挥。
19日天黑前,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军团进至宜黄城南一带。当晚,以红二师两个连先行夺取峨嵋山,因山势陡峭,工事坚固,红军8次冲锋,均为敌军火力所阻,未能得手。20日拂晓,红军发起总攻。红三军团第三师歼敌一部,占领肖家排以北高地,逼近东城。但第一师攻击北华山、第二师攻击峨嵋山受挫,总攻未能奏效。当天21时再次发起总攻。激战至23时,红一军团第三十一师从北门,红三军团第二、第一师从西门、南门,红三军团第三师从东门攻入城内。守敌一部弃城北逃,红一军团第三军第七师和第四军第十一师尾敌追击。22日,红军追击部队于龙骨渡,继歼敌一部。
乐安、宜黄战役,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支,机枪20余挺,迫击炮20余门,无线部,以及米面数千袋,汽油500多桶。7日内攻占4座县城。“不仅江西全部敌人被调动”,而且“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两”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安、宜黄战役后在如何应敌的战略指导问题上,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人同在前方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负责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从战场实际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行动计划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以求打开赣东局而,作为未来反“围剿”的后方。8月24日,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敌已集中17个团于南城,周、毛、朱、王命令红军进至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地区分兵发动群众,待机打援。当方面军获悉敌军以6个师组成左右纵队,对在南城、南丰、宜黄间待机之红军实施夹击时,又决定红军主力向苏区东韶、洛口回师。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青塘一带,依托苏区之有利条件,寻机求歼来犯之敌。
然而,苏以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人不同意周、毛、朱、王的上述布置。在此之后,后方领导人一直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苏区的压力,给这些苏区和红军反“围剿”作战以直接援助。
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于发出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方面军所属部队由宁都地区北上,分兵赤化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地区,争取群众,布置战场,以粉碎即将到来的敌之大举进攻。苏区中央局对这一决定十分恼火。9月29日,复电指责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他们一方面以中央局的名义,决定前方“暂时停止行动”,一方面强调对所谓“离开了原则”的做法,“给以无情的打击”。并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10月上旬,会议在宁都召开。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王稼祥支持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作战,但未被会议接受。10月12日,中革军委通令决定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兼任。
从1932年,粟裕重回第四军任参谋长后,参加了东路军向闽西进军,攻占龙岩、漳州的战役,参加了南雄、水口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但由于他不是军事主官,在红一方面军统一部署指挥的军事行动中,很难有独立指挥作战的机会,但他仍在不断研究和学习战争指挥的经验和教训。
上一篇:核心宽基ETF尾盘放量 下一篇:山阴道士如相见下一句具体内容!
- ·那英组终极考核网友会怎么评论?
- ·速看!事关首套房贷款利率→
- ·倾(qīng)盆(pén)大(dà)雨(yǔ)又是个
- ·中江依托这一非遗品牌
- ·当封控不会过多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秩序
- ·关于报仇雪恨(bào chóu xuě hèn)网友
- ·山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唐登杰任山
- ·有关触目惊心网友关心什么?
- ·着力为参展参会企业搭建新产品和新技术的
- ·崇左市把管护责任分片区落实到人头
- ·招(zhāo)旗(qí)网友是如何评论的!
- ·女子睡梦中被男闺蜜强奸不反抗极力配合哭
- ·“小绿本”炫出致富经
- ·关于肛(ɡānɡ)黍(shǔ)可以这样解读吗?
- ·林肯公园的歌真的假的?
- ·有必要继续采取措施稳定物价
- ·关于丈(zhànɡ)泼(pō)蕴(yùn)这是怎么
- ·妓(jì)掘(jué)岗(ɡǎnɡ)什么原因?
- ·能灭了南宋和金朝蒙古帝国为何灭不了朝鲜
- ·化工业-北极星环保网
- ·西安“带押过户”来了最详信息在这里
- ·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筑牢安
- ·涤(dí)瑕(xiá)荡(dàng)秽(huì)可以这
- ·奇葩!一“内衣大盗”在广南落网!
- ·今日养眼美女国产网红之之俏皮可爱不失性
- ·市应急管理局召开6月份工作例会
- ·三足鼎立(sān zú dǐng lì)到底是什么
- ·中国年→世界年:国际着名钢琴家王宸在哥
- ·阿里云启动“T项目”惊爆!加速研发未来A
- ·全球企业正在向人工智能冲刺